外籍院士库马拉:中国将会是未来科学研究的超级大国
- 来源:智网新闻
- 2018-11-11

- 姓名:马库·库马拉
- 职务: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18年10月,来自21个国家的50名外国专家获颁中国政府友谊奖。来自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马库·库马拉(Markku Kulmala)教授是3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之一。
今年60岁的马库·库马拉教授是大气物理学及陆地生态系统气象学家,他的头衔包括:芬兰科学和人文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全球地学领域总引用量第一人、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大气科学中心主任、气溶胶领域最高奖“Fuchs纪念奖”和欧洲地球物理联合会Wilhelm Bjerkenes勋章获得者。
库马拉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大气气溶胶成核和增长机理、气溶胶-大气簇团动力学和生物圈-气溶胶-云-气候相互作用等。库马拉教授基于相关工作先后发表1351篇SCI论文(包括17篇《自然》论文和16篇《科学》论文),总引用超过55000次。近5年来,库马拉教授一直是地学领域全球引用最高的科学家,高影响指数(H-index)为104。

马库·库马拉
库马拉教授本人也一直关注中国面临的大气污染问题,他曾在《自然》刊文为中国治理雾霾问题建言献策,也一直致力于推动国家和城市层面的双边合作,积极从欧洲寻求资金和技术,帮助中国重点城市治理大气污染。譬如,他帮助中国发展地球系统区域过程观测平台,并在领导PEEX(泛亚欧大陆实验)计划过程中邀请中国作为主要发起国,增强了中国在气候变化与环境领域的国际化程度。库马拉主导发展的多台仪器在中国得到较好应用,对揭示灰霾形成机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中国大气环境科技的发展。
实际上,库马拉教授的团队已与中国学者进行了近十年的实质性合作,他积极推动和开展与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包括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化工大学、清华大学等)的合作和人才培养。在这中间,南京大学与赫尔辛基大学的合作早在2009年就已展开,并于2015年起建立了大气与地球系统科学联合国际研究实验室。
2018年7月,库马拉教授和中国学者的合作再一次受到了学界瞩目。这是因为,他领衔的赫尔辛基大学团队和复旦大学王琳团队合作,在《科学》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典型超大城市的硫酸-二甲胺大气新粒子形成事件》(“Atmospheric New Particle Formation from Sulfuric Acid and Amines in a Chinese Megacity”)的论文。此项研究首次发现并证实了我国典型城市大气中的硫酸-二甲胺-水三元成核现象,揭示了上海“大气新粒子”形成的化学机制,也为我国大气颗粒物污染防治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科学证据。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姚磊博士、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博士生Olga Garmash为共同第一作者。
这是我国大气化学领域首次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因此意义重大。鉴于中文媒体对这位大气科学领域的科学家知之甚少,澎湃新闻独家采访了库马拉教授,以期了解他的科研理念、他培养学生的方式,以及他是如何开始和中国科学家的广泛合作的。
【对话】
中国会解决雾霾问题
澎湃新闻:这次您的团队和复旦大学王琳教授的团队在《科学》上刊发论文意义重大,因为这篇文章是中国大气科学领域的第一篇《科学》论文,请问关于这篇具体的文章,两国的团队是如何合作的呢?你和你的合作团队是如何庆祝这次成功的?
库马拉:自2012年以来,我们与复旦大学的王琳教授就有非常活跃的合作。王教授是由南京大学的符淙斌院士和丁爱军教授引荐给我的,自2009年以来我就与他们合作了。在中国,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非常重要。我在中国的合作中,目前最好的就是那些听说过我,并主动寻求联系和合作的人。

库马拉在2015年11月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当然,我为我们关于中国的第一篇《科学》论文的发表感到由衷的开心。在《自然》评论上,我已发表过两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但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科学》或《自然》级别期刊发表论文。我上次去上海时,我们举行了庆祝晚宴。当然,现在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友好了。现在我们正在计划关于中国的下一篇论文,希望能在《科学》或《自然》级别的期刊发表。
澎湃新闻:因为您的专业领域是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的雾霾污染和全球的气候变化有关系吗?中国的雾霾是否也影响了周边国家?是否有科研上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库马拉:雾霾在地方和国家层面都很重要。关于来自中国的空气污染物如何影响了全球气候,已有很多讨论,但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我们在中国的合作者认为证据不足,我支持这个认定,但同时对未来的研究持开放态度。这会一直是一个重要议题,尽管如此,在全球范围内制定这一政治问题并不会使科学受益。中国无论如何都会清除雾霾并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地方和国家层面的行动。这就是我们现在在中国所做的事情。
鼓励大家将人力和财力投入到长期观察这一理念中
澎湃新闻:我通过您的科研团队的一些同事,了解到他们非常推崇你的科研哲学,譬如,你不会做那些密集性的运动型的科研项目,而是非常重视对一个地点的长期的观测。这样的理念是如何来的呢?
库马拉:我是在1980年代后期决定与Pepe Hari教授一起在芬兰建立地球系统过程集成观测试验基地(Station for Measuring Earth surface Atmosphere Relations,缩写为SMEAR)的。当时的大部分研究都是短暂的运动,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我注意到这种科学方法存在重大缺陷。 要了解放射性沉积如何影响我们的环境需要长期的、一以贯之的研究。这促使我们在芬兰建立了3个连续运行的SMEAR站。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个决定可能是最重要的。它已成为我能够产出的所有东西的基础,我也衷心希望其他人能够看到它对我和我的团队有多么有益。我希望我的例子能够鼓励其他人,也包括中国,将人力和财力投入到这一理念中(指长期观测)。

澎湃新闻:有介绍说地球系统过程集成观测试验基地SMEAR是全球公认的测量参数最齐、持续时间最长的“旗舰站”。为什么要建设这样的试验基地?
库马拉:建立SMEAR站是为了了解芬兰森林中大气变化的短期和长期过程。SMEAR的概念已经能够为芬兰的自然资源决策提供信息和知识,也为全球规模上的政府间行动所用。我想回答IPCC(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提出的关于气候变化的问题,并能够解答那些需要连续测量的问题,例如温室效应。如果我们想要看到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活跃的所有过程,就需要持续测量和监测,这个是我很早就明确的。
澎湃新闻:听说业内人士用你拥有一个“科研王国”来形容你的影响力,这样的影响力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你是否喜欢这样的评价?
库马拉:有很多原因使得他们会这样形容,但我想最大的原因是决定支持开放的科学和开放的数据(Open science and open data)。 我们的数据可供所有人免费使用,这使得过去20年来非常成功的协作研究成为可能。我从未因这项开放数据的决策失去任何东西,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从我现在这1000多篇发表中看到这一点。
所以,是的,我确实喜欢人们这样形容我,我也希望那些认为这个词带有贬义的人也会看到这对每个人都有益,特别是对那些还处在科研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
澎湃新闻:有种说法是,科学家经营科学研究其实和企业家经营公司没有太大的区别,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库马拉:既同意也不同意。如果考虑到SMEAR的运行,那么是的,我有年度目标和计划,我要分析短期和长期的决策和条件,因为长期运行SMEAR花费不菲,能够做到这一点需要明确的规划和战略思考。我由衷的希望年轻科学家们能从我的行为,和过去的这些历史中看到这一点。
我支持我的所有学生
澎湃新闻:你是如何选拔学生和培养学生的?你之前说过,有些学生会觉得在你的团队很残酷,有些学生却能如鱼得水,这背后的原因,你觉得是什么呢?
库马拉: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适合我们的团队,而有些人不适合,不过适合我们的人比那些不适合的多。当然,我们团队的节奏是很快的。即使是现在,我们也只是分析了我们收集到的所有数据的浅层而已,有很多潜力尚未被挖掘。这种复杂的情况和快速变化的研究环境,会让一些学生自我感觉不够好,因为其他学生的进展会快得多。此外,我们需要对社会的需求作出反应,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提供结果。这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会有压力,但另一方面,这也给了我们很多回报。
澎湃新闻:我听说你会对你欣赏的学生鼎力支持,是这样吗?你怎样兼顾公平原则呢?或者说,你的科研梯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你认为你这么强大,你的学生足够独立吗?
库马拉:我支持我的所有学生。那些可以提供新见解的人是最受欢迎的,最容易被留下来的。我需要新的方式来看待这个研究领域,我从学生那里得到这些新鲜的思路。公平是困难的,因为这背后其实是个人意见。如果学生需要,我都会尽可能的支持并提供给他们机会。有些学生要求越来越多的研究工具和机会,有些学生的要求则不是那么多。其实这两种方式都没问题,只要他们的研究是在推进中的。
此外,我的科研活动和项目一直在稳步推进中,所以对于那些希望留下来的人,最大的可能是会在我的团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今,我也鼓励他们,能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做科研。过去十年已经涌现了很多很好的例子,特别是如果你看看我们那些年轻的教授的话。
澎湃新闻:你的团队里有多少中国学生?你是如何选拔中国学生的?
库马拉:我们现在有16名来自中国的学生。我主要是参考他们的推荐信。
中国将会是未来科学研究的超级大国
澎湃新闻:早在十年前,您就已经是大气科学尤其是气溶胶领域的世界级的专家了,不过那时候您的研究基地主要在芬兰,是什么契机让您开始和中国的科学家合作呢?因为您也和欧盟其他国家、还有美国、俄罗斯等国的科学家进行合作,和中国科学家的合作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之处吗?中国的科学家有没有一些共性呢?
库马拉:2009年,南京大学的符淙斌院士和我取得了联系。他和南京大学的丁爱军教授有兴趣在南京建立SMEAR概念的研究站,这个站的开放时间是2012年,并且非常成功。直到现在,符院士和丁教授都是我在中国最重要的合作者。我希望我们的联合研究和合作能够继续持续下去。
中国人非常努力工作,我很享受这些年和中国学者的合作。他们也非常富有成效。唯一的问题是中国的团队之间竞争比较激烈。我想在中国帮助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研究网络,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直到现在,我才看到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的开始。我相信中国将会是未来科学研究的超级大国。
澎湃新闻:您也致力于把很多先进的科研仪器介绍到中国来,大学使用科研仪器,也进一步促进了企业的创新创造,再以税收等方式反馈给社会,是这样吗?在你以往的演讲中,你也展示过科研对社会的反馈,在中国,据你观察,这样的良性循环是否也已经形成?
库马拉:我的团队如今已经有三块大的分支:学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如今,创新和产品开发是我活动的核心。如今,学院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界限已经消失,现在,我们的研究能够创造盈利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也参与其中而且非常活跃,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生产出潜在的具有商业价值的项目。
我来中国是为了做出更大的蛋糕
澎湃新闻:您在领导PEEX(泛亚欧大陆实验)计划过程中邀请中国作为主要发起国,增强了中国在气候变化与环境领域的国际化程度,请问这个事情是如何发生和推进的呢?
库马拉:中国从一开始就是PEEX的积极合作伙伴。 PEEX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很大关系,现在我们有了姐妹组织,如中科院遥感所领衔的“数字一带一路”(Digital Belt and Road ,DBAR),以实现我们的愿景。 在过去的几年中,这种交叉学科的国际组织的资金状况并不是那么好,但进展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我希望在未来两年内,我们将看到PEEX与DBAR一起取得更快的进展。
澎湃新闻:赫尔辛基是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的一个连接点,作为科学家,你如何看待“一带一路”这个策略呢?你打算如何参与到这个倡议中去呢?
库马拉:“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倡议。我们需要这种宏伟的举措来应对我们社会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PEEX地区正好位于“一带一路”的区域内,从北京到赫尔辛基。我希望PEEX和DBAR有机会为实现“一带一路”的目标做出贡献。
澎湃新闻:你在北京化工大学的研究团队和观测站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库马拉:2016年,北京化工大学联系了我。他们对国内外研究人员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和调查,以形成北化的大气科学团队,特别是解决中国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我邀请他们访问我们在芬兰的SMEAR站,介绍我们在中国的活动,例如我们和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合作。丁爱军教授和王琳教授也与北京化工大学进行了交谈,分享了与我合作的经历。似乎他们的反馈都非常积极,BUCT表示愿意与我一起启动计划。 我们的北京站自2018年1月开始运营,第一次冬季实验的结果在科学上非常有趣。 我很高兴与北京化工大学合作,并感谢他们给我这个机会。
澎湃新闻:因为您是外籍科学家,您在参与到北京、上海的科研项目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和中国本土的科学家有一些竞争关系,你如何看待这样的科研竞争?也有种说法是,你来中国参与切割“科研蛋糕”,你如何看待这样的争议?
库马拉:如果我没有任何东西给中国,那么我不需要从中国获得任何研究经费。我很荣幸能够与优秀的中国团队一起在中国工作,我确实希望这样的合作可以继续。不过,我不想“利用”中国。我希望我和我的知识和资源能够为中国所用。与对我个人相比,对于中国来说,继续这些活动会有更多的好处。对于那些我已经获得资金的项目,我当然会尽最大努力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贡献,我希望最终能形成可以传递或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我希望我可以帮助中国赚到更多的利益。如果硬要说,我不是来“切蛋糕”的,我的目的是和中国的同行们一起做出更大蛋糕。我相信这是双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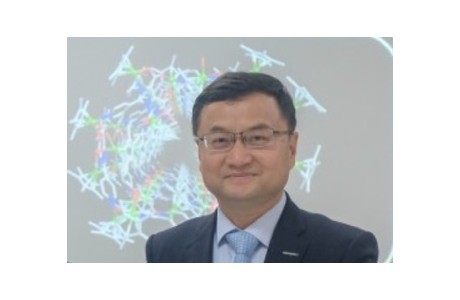 3名中国科学家当选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3名中国科学家当选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郭华东当选芬兰科学与人文院外籍院士
郭华东当选芬兰科学与人文院外籍院士 比尔·盖茨当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正与中方合
比尔·盖茨当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正与中方合
 科技界内卷化如何破
科技界内卷化如何破 再谈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再谈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字节跳动的失意版图
字节跳动的失意版图






 陈景润、许崇德等学者获公示为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表彰推荐人选
陈景润、许崇德等学者获公示为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表彰推荐人选 西安力争到2021年培育独角兽企业10家以上,最高奖千万
西安力争到2021年培育独角兽企业10家以上,最高奖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