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看“仪式”
- 来源:网易新闻学院
- 2016-05-05
“仪式”一词作为一个分析性专门术语出现在19世纪,它被确认为人类经验的一个分类范畴上的概念。所以,这个词的原初所指主要是将欧洲文化和宗教与其他的宗教和文化进行对比。随着仪式越来越广泛地进人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学术研究的交叉视野,来自各种各样的态度、角度、眼光、方法对仪式加以训话和解释者层出不穷,使得仪式的意义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趋势。今天,若人们不加以基本的框限,单就仪式一词的语义就足以令人目眩,其边界也很难确认:它可以是一个普通的概念,一个学科领域的所指,一个涂染了艺术色彩的实践,一个特定的宗教程序,一个被规定了的意识形态,一种人类心理上的诉求形式,一种生活经验的记事习惯,一种具有制度性功能的行为,一种政治场域内的策谋,一个族群的族性认同,一系列时节性的农事活动,一个人生礼仪的表演……大致看,仪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指示:1.作为动物进化过程中的组成部分。2.作为限定性的、有边界范围的社会关系组合形式的结构框架。3.作为象征符号和社会价值的话语系统。4.作为表演行为和过程的活动程式。5.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经历和经验表述。 概而言之,社会的“仪式化”(Ritualization)使得这种现象在社会的许多方面大量出现,分枝越加茂盛,指示越来越填密,形成了一棵茂密的“仪式树”:

今天,人类学的仪式研究已经越来越不同意传统仪式研究上的主导理念和范式:一是以涂尔干为代表的范式,即把仪式当作信仰的行为(“神圣的”或“社会的”)。另一种范式认为,仪式要么是行为的本身,要么只是行为的一个方面。总而言之,将仪式作为一个可以如零件一样从一部机器拆卸下来进行单独分析的、具有器具化操作的样品。当代西方学术界刮起了一股“后学”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种种观念和方法自然而然也循人到了仪式研究领域,并因此产生了一些新的思索点。比如贝尔就提出了一些新见解:首先,由于社会的空前迅猛的发展,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族群交流日益扩大和深人,使得传统的仪式在今天的背景之下增加了许多不同的“新质”。结果是,——亦即最明显的一点是仪式中混杂其他社会的行为和观念。其次,这样的社会进程不可避免地将个人带人到了“仪式化”境地个人的行为都成了“有目的、策略性的”行为。反之,仪式化新产品嵌人了大量属于独立个体的本能性的东西和知识,包括他们的身体、他们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以及他们不得不在维持和平衡权力关系的微妙境遇中作出符合自己理解的行为方式的选择。够通过类似的观点,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福柯、波厄迪等人观点的移植和变形。
文章整理自《人类学仪式理论的知识谱系》彭兆荣,由北大公共传播授权网易新闻学院发布。

在人类学研究的视野范围和意义范畴内,仪式首先被限定在人类的“社会行为”这一基本表述上。广义上说,仪式包括各种各样的行为:从“你好”等日常问候的礼节到天主教弥撒的隆重仪式。利奇(Leach)不失为广义使用“仪式”的代表人物,在他那里,言语(祷词、咒语、圣歌)如同手势和使用器物一样都具有仪式的价值。特纳(Turner)则相对地缩小了“仪式”的范围,认为仪式只属于概述类行为,专指那些随着社会变迁,具有典礼的形式并发生于确定特殊的社会分层。涂尔干则偏向于将仪式视为社会生活的实践过程,而“神圣/世俗”(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的关系和行为被看作完全对立的活动。范·根纳普(Van Gen-nep)的“通过仪式”(Les rites de Passage)被分解为“分离、过渡、组合”的三个程序。他把仪式放置在伴随着地点、状态、社会地位之于年龄变化的过程中来处理,并着重于仪式过程不同阶段“阈限”(threshold)的各自品质、特征以及变化关系之上。正是由于仪式概念和性质具有非常大的伸张幅度和解释空间,因此,它给了人类学家们自主确定其边界的开放场域,即使在对它的基本定义上也是如此;造成了几乎所有对仪式做过研究的人类学家都各自开辟一个自己认为“合适”的领域。众所周知,许多人类学家都对仪式有过不同的论述。“那些包含着世俗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国王和部落祈福的,人们称作为仪式。”“我将仪式视为基本的社会行为。”“仪式是纯净的行为,没有意义或目的。”“仪式是关于重大性事务,而不是人类社会劳动的平常的形态。”“仪式就像一场令人心旷神怡的游戏。”“在仪式里面,世界是活生生的,同时世界又是想像的;……然而,它展演的却是同一个世界。”利奇看得很清楚:“在仪式的理解上,会出现最大程度上的差异。”这种状况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以及将某一款定义搬运到另一个族群仪式行为上去解释,可能会产生重大的歧义,“越是对不同的宗教进行比较,也就越是显得困惑,因为人类的经历上的差异如此的巨大”。然而,至为重要的是:“作为文化原动力的`窗户 ,人们通过仪式可以认识和创造世界。”
今天,人类学的仪式研究已经越来越不同意传统仪式研究上的主导理念和范式:一是以涂尔干为代表的范式,即把仪式当作信仰的行为(“神圣的”或“社会的”)。另一种范式认为,仪式要么是行为的本身,要么只是行为的一个方面。总而言之,将仪式作为一个可以如零件一样从一部机器拆卸下来进行单独分析的、具有器具化操作的样品。当代西方学术界刮起了一股“后学”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种种观念和方法自然而然也循人到了仪式研究领域,并因此产生了一些新的思索点。比如贝尔就提出了一些新见解:首先,由于社会的空前迅猛的发展,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族群交流日益扩大和深人,使得传统的仪式在今天的背景之下增加了许多不同的“新质”。结果是,——亦即最明显的一点是仪式中混杂其他社会的行为和观念。其次,这样的社会进程不可避免地将个人带人到了“仪式化”境地个人的行为都成了“有目的、策略性的”行为。反之,仪式化新产品嵌人了大量属于独立个体的本能性的东西和知识,包括他们的身体、他们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以及他们不得不在维持和平衡权力关系的微妙境遇中作出符合自己理解的行为方式的选择。够通过类似的观点,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福柯、波厄迪等人观点的移植和变形。
人们注意到,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的仪式行为发生在“地球村”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语境之下,仪式的面目一改传统的有确定人群、时间地点、区域特色、文化圈价值等特质,有些仪式越来越呈现出在全球范围内共同遵守某一种“游戏规则”的情形。这样,仪式中的现代“超级权力”已经开始形成。有的学者以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项目为例,认为现代体育完全就是古代“仪式”和“戏剧”的一种延续。其中有一点就是表现出“对权力的迷恋”。奥林匹克运动的仪式化模式大致表现出以下两种文化“再生产”层面的意义:文化的自然的“生性”(habitus)(法国社会学家波厄迪“实践社会学”中的概念)和“社会形象(Social image)。比如女性运动员在体育项目中的“表演”既是“生物的也是文化的”(biology/culture);既是“生物之性也是社会之性”(sex/gender)。人们有理由推断, 今天体育竞赛的“仪式化”活动所遵循的规则已经相当程度的全球化,那么,它的权力也就达到了“全球化”。如果这样的“再生产”得以维持和继续,那么,“产品”也就在“一体化”中流通。仪式不论是手段还是目的,形式还是内容,原因还是结果,这一点必须引起格外注意。
文章整理自《人类学仪式理论的知识谱系》彭兆荣,由北大公共传播授权网易新闻学院发布。


 中国科协发布2020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
中国科协发布2020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 世界五大专利局2019年授权多少专利?
世界五大专利局2019年授权多少专利?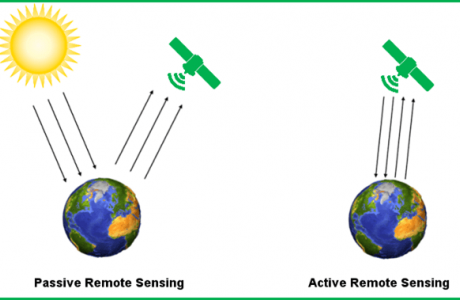 谈谈中国在合成孔径雷达技术上的突破
谈谈中国在合成孔径雷达技术上的突破
 科技界内卷化如何破
科技界内卷化如何破 再谈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再谈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字节跳动的失意版图
字节跳动的失意版图






 展会助力医药企业走向国际
展会助力医药企业走向国际 中国科协支持鼓励科技工作者创新争先
中国科协支持鼓励科技工作者创新争先